�f�ӣ��˻�O�����ǟo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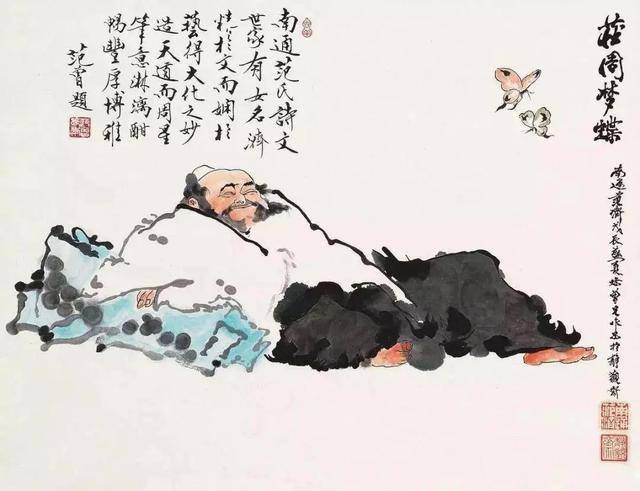
�f�����p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(d��n)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@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ȥ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Ь������
Ҳ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Ұ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иQҊ����Ȼ�ĊW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ټҠ��Q���f���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Ƴ硣
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е��ǻ��c�C(j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ĵ�Į�����˘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ӂ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f�Ӆs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ט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ӂ��Bæ��ጣ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Bȸ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
�f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Nρ�����ڵ��ϱ��B�F���ֺη���
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ߺ���Ӣ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f�ӣ��ۘO�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ۿ�����
�f�ӵ��䵭�o�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һ�N��(n��i)�ڵĻ��_(d��)�cͨ��
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Ո(q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ࡣ
�����T�Ӱټ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v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
һ��(g��)�˳˴��^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
��Ȼ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h��һ�Ҵ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ۿ���Ҫײ���ˡ�
һ�r(sh��)�g���@�˻�ð�������ƿڴ��R��
Ȼ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ҿմ���
�@���L��һ�ښ������ŵ�ŭ����˲�gϨ������
�f���f���f��o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ߣ����oҲ��
�����f�ﳶ��(d��ng)�ľw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fǧ������ի@һ���o��
�෴�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n)��ס�����͕�(hu��)��˴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f�ӡ���߀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һ�����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С��ˤ���ˡ�
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ߡ�
����Ҳʮ���^�ⲻȥ����ȥ�s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T�o���́���
����ŭ��δ����һ�ь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ʾ�ٲ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Ժܴ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@�Ӟ���һ�c(di��n)С�¾Ͱl(f��)����
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?d��ng)ŭͻ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
�f���J(r��n)�飺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^϶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н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Ǻõĉĵ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g����(hu��)׃���^ȥ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Ӌ(j��)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Ű�����ˌ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]�п옷�Ҹ���һ����
�f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һ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Ӽ{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Sһ�а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�О鼺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S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ر��Ƴ�Ҳ�T���f��ʼ�KĮȻ�Դ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ĉ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
���ğo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`��ጷ����ԵČ�(du��)�Լ��Ĵ����
Ҳ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ˎ����
��(d��ng)�҂����Ͳ�ϲ��ŭ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ڟo�n�o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һ�Σ��f��ȥ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ѻ�ʩ��
�˕r(sh��)�Ļ�ʩ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Ɯy(c��)�f��Ҳ�ǁ��\ȡ��λ����
���ǻ�ʩæ�����Ѳ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Ҳ�]�нY(ji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֮�H���f�ӅsͻȻ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Ƚo���v�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Ϸ��зN�B�����g�R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ͩ��Ͳ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Ĺ���(sh��)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Ȫ�Ͳ��
�����Ϻ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һֻ؈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؈�^���Ԟ��g�R�ǁ퓌ʳ�����͌�(du��)���g�R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Ҳ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퇘���҆�����
��ʩ �T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sҲ�o���Ԍ�(du��)��
���^ �f���@ô�S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߀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Z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f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ďā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f�Ӻͻ�ʩ�����ˮ߅��
��ʩָ��ˮ�е��~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옷ѽ����
�f�����̷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ô֪�������옷����
��ʩ����һЦ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֪�����Ҳ�֪���~�Ŀ옷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Ԟ��q�^���f����
�l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f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Ҳһ�����˽��~�Ŀ옷����
���c�˵ĸ����Dz�һ�ӵ����옷�c��ֻ���Լ�֪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ӭ���l��Ҳ����̫�^���顣
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Ҫ�m��(d��ng)?sh��)؍�¶�hâ��
�f�ӵIJ������飬�nj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x���nj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ĸ��ᡣ

Մ���f�ӵġ��o�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ߴ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т�ǰ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ѡ�
���f�Ӆs�P�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質�裬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n����
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ゃ����һ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߀���裬̫�^������
�f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e(c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݆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ٌ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
���@݅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ӵ��^���x���e���c����c�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_��
���ֵ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˴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f�ӡ����ڎ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ǃɗlС�~��
һ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ɗlС�~�R�\��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ĭ�흙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˄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
���f��Ҋ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Ⱥ�ˮ�q�M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λ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֮�a���Ҵ���߮��ãã�˺���
�ِ۵��H�����ٺ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^��
��(du��)��ע��Ҫ���_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p��ֻ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p�@��
�x��ѣ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˷քe�r(sh��)�̵�ʹ�ࡣ
�~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ڕr(sh��)�g��
�f�ӵğo�����̕�(hu��)�҂����ǽ�Ó��
���f�ӡ��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d��һ�κ������Č�(du��)Ԓ��
��ʩ˼ǰ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X���f��̫�o����
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Ǜ]����Ć
�f���f���ǵ���
��ʩ�ְl(f��)���`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ô�ܷ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f��˼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L���f��
���f�ğo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Ҫ�p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ڵı�����Ҫ협�(y��ng)��Ȼ��
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ӵ��@ЩԒ���o��(sh��)�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
���У��ұ��^�J(r��n)ͬ�ϑ���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f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Եğo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
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ľw���o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b���@��һ�N���ǻ���
ҲԸ�҂�?c��)��՟����@�ǻۣ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(p��ng)Փ �u(p��ng)Փ (4 ��(g��)�u(p��ng)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