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�����p��] 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 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ĕr�����D
��2 ���� 86 ����x 2024-08-30 11:01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 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ĕr�����D
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LՄ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˼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̄�ӡ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о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ҏ�����Ůʿ�Ƴ����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ʿ�v����ʮ�꣬���L�˶��ٶ�λ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Тͨ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ߺͿƌ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r�ڵ���Ҫ�vʷ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ȫ��λ���x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ĵ�һ��ҕ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Ѻ��Ļ��ؼs�������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v�̺Ͳ��L�r��һЩ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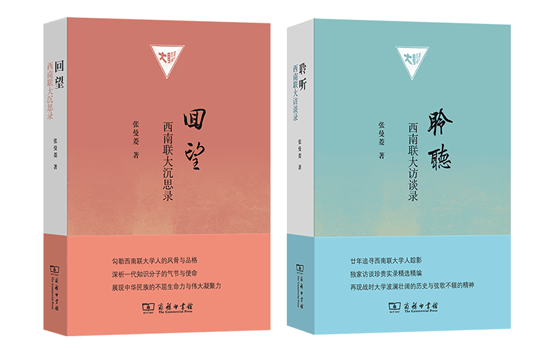
�Ѻ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ڌ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ՄՓ�^���r�g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˒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صĽ��Ϛ�Ϣ���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r�£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~�ܴ����Y���@���~��l(f��)�˚w�l(xi��ng)֮˼���L���h�h�����֞t�t�����՚w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䌍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׃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Ǽ��l(xi��ng)�ľ�ɫ���t�˙������G�˰Ž���
��һ�λ؇������ǔy�����Ĺǻ���Ҫȥ�K�ݵ����Ĺ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e�w�ć@Ϣ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Ќ��ƌW�c�Ї����ĽY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ƌW�^�v���Ї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족�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⡱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R���r�g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܇���һ�ж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á����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ꎡ���Ҫǡ����
��ȥ�^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ʂ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ψ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᷌O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WУ��Ҫ�Ƅ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]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_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;�����Ō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Ǖr�����w�ѽ�˥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韩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˒������@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݅�ľ�ʾ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K�ݣ����ԡ��w��ϴ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
�Ѻ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ö��ͬ�r�ڵ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ՄՄ�@��öУ�յľ��wԢ��ô��
�����⣺ 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ˡ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㌦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ץ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ö���շ��M�ҵ����ġ��܇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^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ö������һö�njW���£�һö�ǽ̆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ഺ�c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

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յı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̖���@��̖�a�nj����WУ�n���ġ�
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ڡ��ĕr���Һ÷���һ���PͲ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
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֪���ܶ��W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I(y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ٛУ�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ֱ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\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Մ�Ĺ��¶����Кvʷ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ϱ����ǷN��ʷ�ܲ��ּҵľ��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҂���Ԓ�}�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ӑՓ���µ��Ļ���r�c����Σ�C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҂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d����ϲ�g����ՄԒ����
�o�Ƭ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ʾ䛡��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nj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vʷ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Ƶ�֧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ۼ����ؕr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õģ������˺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Ǖ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Ҽć��D���R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úܴ���
���Ҳ߄�ȥ���L�_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W�˵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Ą��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Գ��е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Ҫ�@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Ҹ��H�^�����Ҍ��ˡ��Ї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ҵľ���ԴȪ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Ї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o���D���f����ֵ���ղ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N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ɞ��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ů�c������֧�c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õġ��W�ꡱ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˵�Ʒ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q�ء��⹝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c�Ը����ڇ��y֮�r��Ȼ�x���Ї��܌Wʷ����K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ĥ�y֮�У����ĈԶ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ͽo�����ă�ö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һ�N���W�}���С�֮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Ļ��߳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ŗ����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ľ��빤�����@һ�c���ҵ�Ӱ푺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vʷ��ǰ����Ҳ�ʮ�һ�uһʯ��
�Ѻ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ڕ���Ԕ���v���˄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W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HҲ���Մ���^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Щ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ӡ����^�
�����⣺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Ą��ĵ��Ȥ����̫�A���ڊʘ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ľ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ġ�����v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Ҫ߀ԭ���ı��|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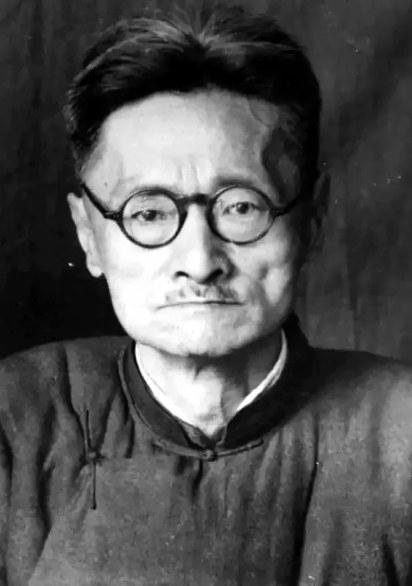
���ĵ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Ԓ�ǣ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�մ�W��Ȼ���в�Ԫ��ġ����ݲ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P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M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��_���Y��ʯ��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]���桰�ߡ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ǽo���Y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ߵĹ°��Č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ȥҊ��У�L��Ԫ�࣬��Ҋ�����г��ĵ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S������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c��ؓ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ڑ�(zh��n)��֮�H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ărֵ��ֵ�ò�ֵ�û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ʲô���@��ҕ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ÿ��֪�R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Zը�dz������ĕr����ÿ��Ҫ�s��܇ȥ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˓��Ą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Ԓ�����Ҍ��ɱ�ը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ȱ�n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Ї�����Ҫ��
�Ѻ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У���÷�O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ܳ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x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�ʲô��
�����⣺���J��÷�O����һ�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y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⹝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w��(li��n)�ϵľ���֧����÷�O�����hҊ����ǰ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ƵĽ̌W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У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^���njW���c�WУ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н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һ���t�ǡ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Џ��ҵĸ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;���Pע�_���ˡ����ҡ�֮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ᗉ���A�@���m�ļ҈@�Ͷ���e���Ĺż�һ����֮�r���e���О�֮��ϧ�����s��갿˼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һ��Ƭһ��Ƭ�āG�����ױ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
���_���@�ӵľ���߶ȣ��c��ԭһ�}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ǡ�ͬ�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܉����۲�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Ę˗U�Ե����һ��H�܉�鲽�ЈF�����̖����ȥ�J�R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I�r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ЈF�ߵ�һ��С�h�ǣ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Q200���˵�ʳ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LҪ�[��ϯՈ�̎�ȥ�ԡ��W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վ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ʾҪ�c�W��һͬ���I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ƽ�o���@һҹ�����ȶ��]�гԛ]��˯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ڿ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ʳҲ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Бcף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ĿsӰ���춨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ăȺ�����һ��ɞ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еČ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˸߸ߴ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h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@�ӻؑ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W�g�ϵČ�ע�c�_�ء�
һ�������ԫ@�á��η�һ�ǡ����˵ľb̖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о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Ƴ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o�Ї���Ԋ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˜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[Ó��̼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q�¡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һ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c���w�Ľ��v����I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W�g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kһ�ݿ��ʮһ�����ᳫ�c�о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ķ�˼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
һ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N���S��ļ��Ͽ�Մ���@�N�⹝(ji��)��Ҳ�w�F(xi��n)�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ɵ�Ѫ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Ԏh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ͬ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x��
һ��Ĵ��ڪq�硰�t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c��ů��
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c���ҵ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Ě⹝(ji��)��Ʒ�|����һ·�߁���ɢ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Ӱ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f��ȥ��
�Ѻ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δ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˼䛡��Ѕs����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Ŀ����ͻؑ���Ո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ӵĿ��]�ڕ������뼾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Ǻ���Փ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⣺�Ҍ����w�ּ{�顰���P�W�ߡ������ڃ��c��
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ע�����㡵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ɌW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Փ�ļĽ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ꐵ����]���M�뱱�Ĵ��_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|���Z�ԌWϵ��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~���f�Լ������㡵ġ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Ё��^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H�ܵĎ����P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^ʳ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��⣬���Ǐġ����҂��С��@���Ƕȁ��f�����@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ʷ�W�г��õ�һ�Nҕ����
�ڼo�Ƭ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ʾ䛡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F(xi��n)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ǵ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Ӻܴ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ʾ��ʹ�˂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⹝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ˌW�ߵĵ�һ���P��
���w��߀�c���m���H�ܵ��Pϵ���ڲ��L�У���Մ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ȥ�Һ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㡽�Q����ȡů��Ѻ�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ư��š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ǰ߀�]�п����^��
���w����Մ�ă��ݣ��DŽe�˲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vʷԪ�ص�һ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c�����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ȫ�汬�l(f��)�r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ǂ��r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ʡ���Ǟ����y�õ���W��僽𡱙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]���܉��c�����ĸУ���H�˹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Ŀ��y���@Ҳ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ăȾ��c��؟��
���Ľ��v�c�����ꌦ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Ї��W�˵��`�ꌑ�ա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Ƭ�vʷ�У���һ�N�^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⣬�h������؞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1978 �������뱱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ϵ��1982 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@�����^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ƪС�f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Ƭ�S�ľ����Ӱ���ഺ������1989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Ϗ���Ӱҕ�I(y��)��1992 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k����ˇ�g�l(f��)չ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Ĕz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Ƭ��֪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1998 �꣬������ʡί�˲����M��ͬ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o�Ƭ�Ŀ��2003 ��4 �����o�Ƭ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ʾ䛡�����ҕ��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ڮ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傀һ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2013 �������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˼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ʾ䛡���2018 �꣬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ּ��ϾW(w��ng)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}��(sh��)��(j��)�졷�����С��Ї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ؑ�����ɢ�ļ���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1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