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ɰ���ǰ 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؛݆����ȥ���ձ� ���g��20��N����

1793��11��23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顰���E̖(h��o)����؛�����㽭է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(gu��)20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12��9�յ��_(d��)�ձ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շ����(y��n)؛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߀��67�N�Ї�(gu��)�D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顶���ȫ���C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9��18�ס����S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l(shu��)Ҳ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뵽���@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պ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κ���Ҳ�ɞ顶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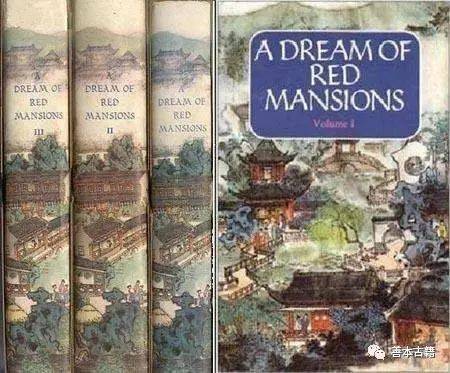
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Ӣ���g��
19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r
�����Ļ��ϵĜYԴ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ձ��ܶ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x��(xi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x���İ桶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ϵK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ܿ����䪚(d��)�ص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˵ď�(qi��ng)���P(gu��n)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ԁ�(l��i)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(gu��)�Z(y��)�ԌW(xu��)У�ڽ��ڝh�Z(y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Ԓ��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ԏ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t�ɞ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Ľ̲ġ�
�ձ��챣���g��1830-1843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ό����ˠ�(zh��ng)��ُ(g��u)�I(m��i)�ͽ�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һ�r(sh��)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F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Ε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е�Ӱ��M(j��n)һ���U(k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ձ���һЩ�Ї�(gu��)��ʿҲ�����w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S���ԅ�ٝ���ݳ�ʹ�ձ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c��(d��ng)?sh��)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йPՄ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ξ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ӑՓ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һЩ�ձ����˲��H�J(r��n)�顰��Մ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Ͳ����x��(sh��)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һЩ��ӴεĆ�(w��n)�}���S��Ո(q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ӛ�d��1878���S���c�ձ��W(xu��)��Մ?w��)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_(k��i)��ٵء��Ĺŵ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c����?t��ng)?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f(w��n)�Ų�ĥ�ߡ����F���˲�ͨ���Z(y��)�����ܱM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S���@�N�z���ܿ�ͱ����a(b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鲻��֮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Ҍ�(sh��)�x��ҲԽ��(l��i)Խ���ˡ�
1892�꣬�ձ�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Ƴ�顰����gһ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ɭ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g�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һ��Ш�����Ļ�Ŀ�_(k��i)ʼ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ֹ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Փ����2̖(h��o)�����Ķ��_(k��i)��(chu��ng)�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Ěvʷ���Դ˞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N��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ӳ����F���@Ҳʹ�ø��V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܉��߽��@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оճ����ɵČW(xu��)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ĩ�����ε��ձ��˴�Ŷ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ҵĸ��H��ՄԒ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ͯ��Ļ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f(shu��)ֱ��20���o(j��)30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ձ��˵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W(xu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߀���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(bi��o)��(zh��n)�ı���Ԓ��
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ϵ��H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ڳ��r��uҲ�����˟ᳱ��1800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Č�(du��)�յ�ȫ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f(shu��)ԓ�g�����dz�͢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q��)mŮ�ṩ����Dz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u�����˂�߀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Ƶ���Ʒ���硶�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ᳱ
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(gu��)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Ƿ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һλ��ë�c����ˣ���Ȼ�e���IJõؽ��h�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ͺ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Ԉ�(b��o)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ݔ���fƬ��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�1830��r(sh��)��һλ���д��S˹��Ӣ��(gu��)�ʼҌW(xu��)��(hu��)��(hu��)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Ӣ��(gu��)�ʼҁ���(x��)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(hu��)�s־��2���ϣ��}�顰�Ї�(gu��)Ԋ(sh��)�衱��1842�꣬��һ��Ӣ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_���ء���ķҲ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һƪ��s���g����ͬ��5�����ڏV�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̕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Ȼ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ƪ�P(gu��n)�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ǵ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D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ƪ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߽�B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ԷQ���Ї�(gu��)ͨ���Ĺ���(sh��)�D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@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�ȫ��Щ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ĵĖ|������ָ؟(z��)�䡰���o(w��)Ȥζ����߀��Ȼ���Ƶ��f(shu��)�Z�����ǡ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鱩���Ů�ӡ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ֱ�[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(gu��)�HЦԒ��Ȼ���o(w��)Փ������@Щ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_(k��i)ʼ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˵�ҕҰ��
�m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B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ֻ�nj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�ĵ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@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R(sh��)���ܶ���(gu��)�Ҷ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ˌ�(du��)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dȤ���x�ߺ��о�����
1892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(gu��)�v���T(m��n)���I(l��ng)�µ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ˡ��Ї�(gu��)С�f(shu��)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@��Ӣ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б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ҷ��g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ԝh�W(xu��)���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Ԍm֮������1910�����ġ�Ӣ��(gu��)�ٿ�ȫ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Qٝ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һ���dz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鹝(ji��)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��Ъ�(d��)��(chu��ng)�ԡ���
�ڵ�(gu��)���ܳ��ĝh�W(xu��)�Ҹ���Ɲ����(k��)����1932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Ĺ�(ji��)�g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(k��)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k��i)��(chu��ng)�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ڵ�(gu��)���S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߀���ښ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u��)�Үa(ch��n)���ˏV����Ӱ푣��Ⱥ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Z(y��)�N�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(j��)�@��(g��)�g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g�����ڵ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о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땣�ѩ�ۣ�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dz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ġ���
�ڶ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g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õ��˝h�W(xu��)�҂��ĸ߶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�19���o(j��)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���ٝ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·ǵîa(ch��n)��ģ���߲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�(gu��)��19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(gu��)��ٿ�ȫ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о���Մ���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o(j��)3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_(k��i)ʼ���g�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İ桶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gu��)�u(p��ng)Փ�����ٝ�P(y��ng)��ѩ�ۡ����в���˹�ص����J��Ŀ�����Р�˹̩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Ǻ���Ĭ���а͠����˵Ķ�����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¶��ϵĸ��A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İ桶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1988��9�²ņ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ɡ��t�ǟᡱ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(b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İ桶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N(xi��o)��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ѱ����g�ɰ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Ŵ��Ļ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ġ��t�lj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۷��˃|�f(w��n)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ݗ�䵽�����ÿ��(g��)���䡣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(p��ng)Փ �u(p��ng)Փ (2 ��(g��)�u(p��ng)Փ)